
1989年,我带着彷徨提前一年从清华大学毕业。当时清华是五年制。大三时,父亲出车祸意外离世,给了我巨大打击,我的世界观、人生观都因为父亲去世而被完全颠覆。
第一次叛逆
1987年9月21日下午6点多钟,父亲在骑车回家的路上,被一名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司机撞倒了。司机人还挺好,第一时间将父亲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。当时父亲昏迷不醒,只要施救,肯定会活下来。可急救室的一个医生告诉出租车司机,施救之前要先缴500块钱押金。这名司机急急忙忙开车出去筹钱,当时是6点半,晚上11点时他拿了500块钱回来。
1987年,能筹到500块钱不容易。缴了押金,医生开始施救,但父亲的血压已经测不出来了,脉搏也没有了。而在此之前,父亲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4个多小时没有人施救。
父亲的离世让我不知道今后的路该怎样走。那是我第一次叛逆。从小父亲就想让我做工程师、科学家,但这件事之后,我会想:做工程师、科学家有什么用?父亲倒是工程师,却落了这样一个下场。当时的我就想留在中国改变现状。
因此,毕业时我并没有出国的打算,而是和清华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签了协议,代表清华大学去香港工作。但由于一些特殊情况,香港方面表示无法履行工作协议,我只能放弃了。仓促之间,我做了一个决定:考托福出国留学。
决定出国以后,我就拼命地复习英语,英语当时是我的短板,成绩一般。我就这样跌跌撞撞去了美国。
指出导师错误
到美国后,刚开始我也很不老实,经常关心课堂外的一些事情,经常想在国内的事情,也在看周围的事情,做了很多其他人难以想象的事情,比如去餐馆打工近一年。
直到1992年,我读到博士二年级,才开始有了一点感觉。那时,我发现自己在实验室稍微努力一些,也能学得不错,研究做得也还可以。1993年时发生了一件比较意外的事,让我发现自己学生物还是有一定优势的,因为我的数学和物理基础比较好。
我的导师是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家,不苟言笑,我们都很怕他。有一天,我们开小组会,他非常激动,开始在黑板上推演,向我们展示他自认为发现的一个生物物理学中的重大理论突破。推演到最后,他写了一黑板的推导公式,告诉我们:热力学第二定律是有问题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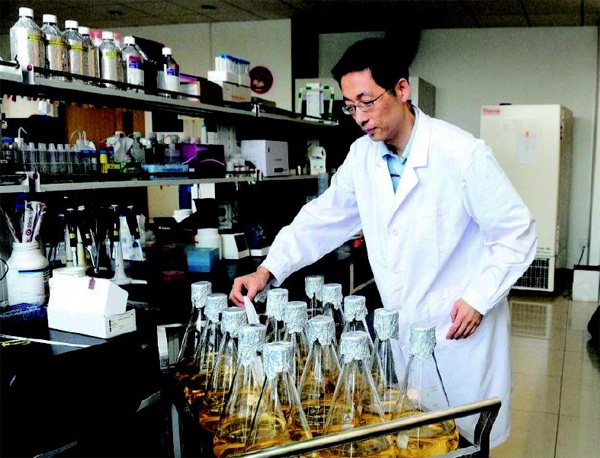
当时,实验室里有二十几个人,十几个博士生,六七个博士后,都坐在那里听他讲,大家听得目瞪口呆。恰好我的数理基础很好,公式推导是我的强项,在他推导的过程中,我已经发现他犯了错误。他讲完以后,我已经看到3处错误,当时实验室的同行没有一个举手的。我当着众人的面,跟导师说他的公式推导过程中什么地方出了问题。说完之后,我有点担心自己惹祸了。但下午再见到导师时,他却向大家夸赞我,说:“这么复杂的推演,你能在瞬间看到问题,真了不起。”他的夸奖让我心里开始放松,也意识到自己学习生物学的优势。
被动转为主动
1995年,我博士畢业时,已经深信自己将来做生命科学研究,谋生没有问题,但还没有自信一定能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科学家。所以,毕业时我又犹豫:自己究竟需要做什么?想做什么?我是一个让思维顺着感觉走的人,不愿意禁锢自己。所以,毕业后我跟朋友在巴尔的摩市成立了一家公司,希望促进一下中美贸易,把中国没有的技术通过我们的中介带到中国。
做了四五个月,发现挣钱没那么容易。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,自己的长处不在做生意,而是用自己的脑子做研究。到1995年夏天时,我决定,自己这一辈子非生命科学莫属,而且确定了方向后再也没有变过。
我的学术启蒙地应该是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。清华大学教给我一些技术知识,但当时在研究上我真的是一窍不通,没有研究理念,也不懂研究方法。在清华,我受到了清华观念的感染和清华精神的熏陶,但我依然不知道怎样从被动地接受知识转化到主动地寻求知识。这步转化最终是在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期间完成的。
知道怎么爱国
对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,对巴尔的摩,对在美国留学前几年的生涯,我是非常留恋也非常感慨的。在那里,我不仅学到了知识,还学到了科学研究的方法。在看导师、同学、同事做科研的过程中,我有很多机会跟他们交流,耳濡目染,逐渐把科学研究的方法学到。这是我在巴尔的摩最大的收获。
国内的本科教育偏重于知识灌输,偏重于让学生记住很多知识,却没有花时间告诉学生,知识是怎么来的。我们没有给学生讲科学史,这非常重要的一环在我们的教育中是缺失的。我们没有讲发现知识、建立体系的人是什么样的人。学生必须知道他们是什么人,才能破除迷信。
我在清华开了一门课,每年秋季给学生讲科学史,我会把科学家的生平、一些重要的事件、关键的实验全部穿插到课程里面,让学生觉得非常有意思。开这门课有几个目的:一方面让学生破除迷信,认识到科学家也是人,再优秀也还是人,不是神;另一方面让学生真正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,为什么会这样,自己能不能做到,等等。
出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,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:我以前也很爱国,但有时候有点偏执,总从自己的角度考虑,觉得应该怎么样,还会抱怨一些事情。到了美国后,我有了另外一个视角,比如去了解美国人怎么看中国,美国社会怎么运行,我开始意识到另外一些事情。还没有出国时,我对爱国的看法经常是片面的。所以对我而言,不出国,就不知道怎么爱国。
(祈梦真摘自中译出版社《海归者说:我们的中国时代》一书)









